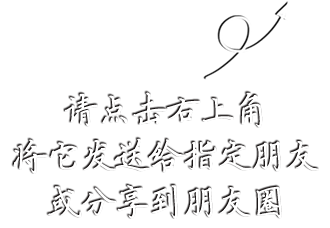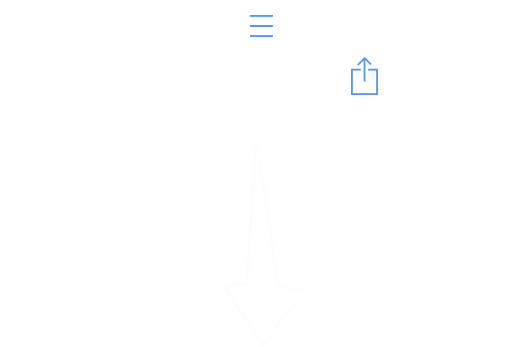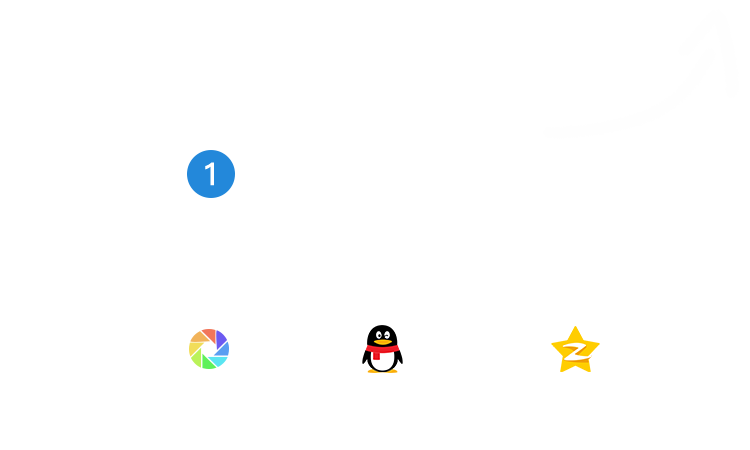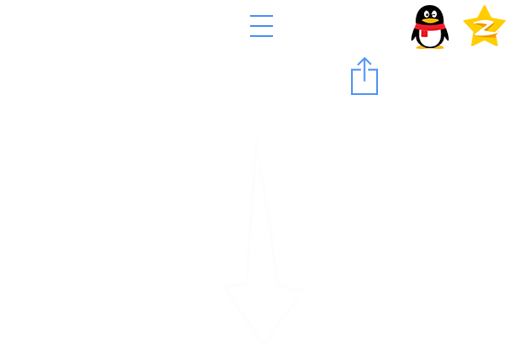中国哲学史(蔡元培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
宋志明

哲学史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在哲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可以有学术思想史书写,并没有哲学史书写。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有联系,也有区别。学术思想史的外延比哲学史大,历史比哲学史长。只有当“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哲学史学科建设才有可能。20世纪初叶,哲学在中国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史也随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且逐步同中国学术思想史区别开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正是蔡元培先生。1“哲学”一词是希腊语“爱智慧”的译名,出自近代日本学者西周。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有“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说法,西周从中受到启发,把philosophy译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后来简称为哲学。1874年,他在《百一新论》中写道:“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1]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术语,但有类似的说法。在中文中“哲”就是“大智慧”的意思。《尚书·皋陶谟》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孔子在临终前慨叹“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这里,都用到了“哲”字。尽管“哲学”一词是外来语,但哲学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宏观的意义上说,哲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古代哲学,指的是“一切学之学”,即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广义上的哲学。另一种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这是一种狭义上的哲学。古代哲学家并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他们的哲学思想虽没有以哲学形式出现,但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没有“哲学”这种称谓而已。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同视为东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类似,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那时哲学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西方哲学史都是近代哲学家编写的,都是哲学家关于学术史的哲学诠释,并不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在中国古代,没出现“哲学史”这门学科,在西方古代同样没有出现这样一门学科。
对于 “爱智”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人在17世纪就已经接触到了,并译为“爱知学”。1631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傅泛济意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开宗明义首论“爱知学原始”,写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 又说:“译名,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刻本)使用“哲学”一词。近代中国学者虽然接受了“哲学”这一词汇,不过尚未认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例如,1901年蔡元培写《哲学总论》时,仍旧认为“哲学为综合之学”,“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爱智”同中国“弘道”“穷理”言殊而旨同,中国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哲学”一词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存在着文史哲不分、经史子集不分的情形,其中《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等著作,都明显地包含着哲学史方面的内容。2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的外延虽然可以重合,但毕竟是学术思想史中的另类。哲学史是哲学成为独立学科以后,有哲学素养的研究者从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出发,运用哲学史研究方法,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提供的材料,建立起来的新学科。哲学史有别于学术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哲学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西方17世纪中叶,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出于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开始有人编纂哲学史。于是,西方哲学史随着哲学学科的出现,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近代哲学家通常用讲哲学史的方式讲自己创立的哲学,历来有“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说法。西方哲学史的作者,即便不是黑格尔那样原创型的哲学家,也是经过系统哲学训练、有哲学学养的学者。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可以说是比较强的,历来有后朝人为前朝人修史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前人为我们留下大量的精品佳作。庄子著《天下篇》,荀子著《非十二子》,韩非子著《显学》,司马谈著《论六家之指要》,朱熹著《伊洛渊源录》,朱熹、吕祖谦著《近思录》,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著《宋元学案》,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江藩著《国朝宋学渊源记》,章太炎著《訄书》,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为学界称道。这些学术思想史名著为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不能把它与中国哲学史等同起来,因为后者出现较晚。只有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才具备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条件。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方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脱胎出来,有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史。
“中国哲学史”的称谓出现于20世纪初叶。191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中国哲学门,便以“中国哲学史”为主干课程。初期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有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等人。他们讲授的课程,名为“中国哲学史”,实际上讲的还是学术思想史。他们没有树立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也不掌握哲学史研究方法,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领域。陈黻宸说:“儒学者,乃哲学之轨也。”[2]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描述陈黻宸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情形:“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3]按照冯友兰的描述,陈黻宸所讲的内容,显然不能算是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是第一位编写题为《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不过,他写此书的时候,也没有认清哲学的学科性质。他的看法与陈黻宸相近。他说:“儒即哲学,伎即科学。官学失散,乃谓之儒学,谓之道学,谓之理学,佛氏谓之义学,西方谓之哲学,其实一也。”[4]谢著《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此书虽名为中国哲学史,实则为中国学术史。作者没有树立哲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仍沿用以往的学案体例,对每个思想家的言论做了一些梳理,并没有从哲学角度做理论分析和评判。诚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此书不够“哲学”,算不得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此时“中国哲学史”学科,只有其名,尚无其实。陈黻宸、谢无量等人可以称得上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先驱,但他们毕竟没有真正迈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有人反对“胡话胡说”,主张“中话中说”,主张回归陈黻宸、谢无量的讲法,重现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史”。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没有任何益处。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与此相应,哲学史也是不断发展的学科;因而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亦需要不断地探讨和创新。若想“回到陈黻宸或谢无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3在西方,哲学学科意识是在近代明朗起来的。在中国,对于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则是在现代逐步明朗起来的。在西方17世纪,哲学便成为独立学科;而在中国,20世纪初哲学才成为独立学科,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学科意识,是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而形成的,走了一条捷径。最初意识到哲学并非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的学者,就是蔡元培。他是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12年,他在留学德国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民德杂志》创刊号上,1913年4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全文转载。从此文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学科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把哲学理解为“综合之学”,而是理解为各门具体学科分化出去之后的独立学科。
1915年,他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在国外撰写《哲学大纲》一书。他参考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树立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哲学为学问中最高之一境,于物理界及心理界之知识,必不容有所偏废,而既有条贯万有之理论,则必演绎而为按切实际之世界观及人生观,亦吾人意识中必然之趋势也。”[5]123在后来出版的《简易哲学纲要》一书中,他对哲学学科性质做了这样的解释:“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5]395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蔡元培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他已经认识到,在各门学科独立发展起来以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不断深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他对哲学的看法,突出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透出一种理性主义的眼光,折射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他强调,哲学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是僵化的教条,任何停止的论点都站不住脚,谁也不能以为自己达到了顶峰。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清楚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但不同意把二者对立起来。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是对待的,而是演进的。”[5]311科学为哲学提供前提,但人类自有一种超乎实证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要求。科学出现后,哲学依然有独立的发展空间。蔡元培把哲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三个:一是认识问题,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适当、认识的对象等内容;二是偏于世界观方面的原理问题,涉及实在论、生成论等内容,由此形成“理论的哲学”;三是偏于人生观方面的价值问题,涉及价值、伦理、美感等内容,由此形成“实际的哲学”。他还指出,以科学为前提的现代哲学,同古代哲学的区别在于:不再受到宗教的限制,甚至具有取代宗教的功能。他大力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概括起来,蔡元培对哲学学科的看法有三个要点:第一,哲学是关于认识论的学问,应当诉诸理性,讲究逻辑证明,不能建立在“圣言量”上面,不能以引证代替论证。第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提出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理论。第三,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帮助人们树立一种指导人生实践的价值理念。基于对哲学学科的新认识,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创办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哲学系。他的哲学观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立了理论基础。
4在现代中国,最初迈入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者,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一批在西方接受过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在他们之后,有些在本土完成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如张岱年等人,也加入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者的队伍。这些学者同陈黻宸、谢无量等人的区别在于,都有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不再沿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都努力探索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之路。
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但正是由于他倡导自觉哲学学科意识,才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成为可能。他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对中国哲学史课程加以改革,大胆起用刚刚从美国回来专治哲学的胡适担任主讲教师。胡适以哲学学科意识为指导,更新教学内容,把中国哲学史同中国学术思想史区别开来。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取得的第一项成果。
蔡元培亲自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对他的学术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胡适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梳理中国哲学史,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做,便无法跳出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便无法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便无法找到表述哲学史的合适方式。“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虽然用了“依傍”两个字,只能说用词不当,并非主张“以西范中”。在他看来,哲学史乃是哲学家对学术史的哲学解读,因而借鉴西方哲学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十分必要;只有如此,方能理出中国哲学史的头绪来,方能突破学术史的表达方式。
他对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予以充分的肯定。他为胡著做《序》,认为该书有四点突破。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引证前人的言论为依据,绝不盲从不可靠的传闻,善于用心考辨研究对象的生存时代、思想的来源、著作的真伪,善于从学理上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中是否存在矛盾。“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有建立学术规范的意思,也起到了示范效应。研究哲学史的任务,既要摆事实,更要讲道理;既要介绍古人说了什么话,还要解释古人为什么说这些话。研究者必须有所“见”,提出自己的观点,还对自己的观点做出充分的论证。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胡适已经突破学术史研究的路径,专题研究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史料中提炼出哲学思想,梳理出头绪来。作者一改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讲起的路径,“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这意味着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史,有别于以往的学术史。哲学史选材要精,不能杂,不必包罗万象;哲学史选人要准,只选有文本依据的哲学家,不必考虑他名气的大小。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胡适撇开以往流行的道统观念,不抱任何门户之见。他把每个古代哲学家都当成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崇拜的对象,既同情的了解、也中肯的评判,绝不厚此薄彼。在他笔下,“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这是很大的突破,真正找到了历史感。在道统观念中,只有尧、舜、禹、周公、孔子才是树立道统的权威;至于后来学者,或者是道统的继承者,或者是道统的疏离者,绝不是道统的推进者。如果不破除这种道统观念,怎么可能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揭示出来?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胡适找到了哲学史的表述方式,改变了以往学术史表达的“平行法”。在胡适笔下,哲学家的诸多思想侧面是有联系的,“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6]。哲学史是对学术思想史的哲学解读,而解读的方法就是做系统的考察。用系统的方法揭示哲学家实质的思想系统,具有创新的意义,至今还是研究哲学史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初建阶段,取得的第二项成果是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如果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山之作,那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堪称扛鼎之作。此书的影响力已经走出中国,遍及全球。荷兰裔美国人卜德与冯友兰合作,将此书译成英文,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国外汉学家大都是借助这本书,对中国哲学史有所了解的。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曾回忆说,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对她有很大影响。第三项成果是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大部头的专论。
以上三项标志性成果的取得,皆同蔡元培在哲学观上的引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蔡元培的影响下,这样一批有哲学素养的学者,从现代哲学观出发,摸索到一条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路径,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1916年,蔡元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系,至今将近100年了。笔者认为,在这段历史区间,学科建设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以前,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学科建设落入低谷;第三个阶段为1978年以后,迎来学科建设的春天,开始复苏。总的来看,呈现出马鞍形发展轨迹。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开拓者的论著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全盘否定他们的理论思维成果,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将他们粗暴地赶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教条主义者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以苏范中”,陷入“两军对战”的误区而不能自拔,致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走上歧途、落入低谷。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极其惨痛的,我们应当牢牢记取。我们也不能像虚无主义者那样,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把前辈的贡献一笔抹杀。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贡献,研究他们的贡献,超越他们的贡献,沿着他们开辟的方向往前走,踏上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卞崇道,王青.明治哲学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3.
[2]陈德溥.陈黻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415.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0.
[4]谢无量.中国哲学史[M].上海:中华书局,1916:1.
[5]蔡元培.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