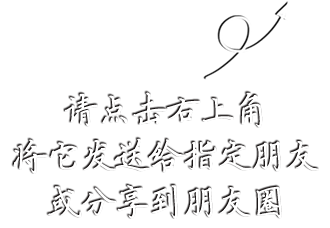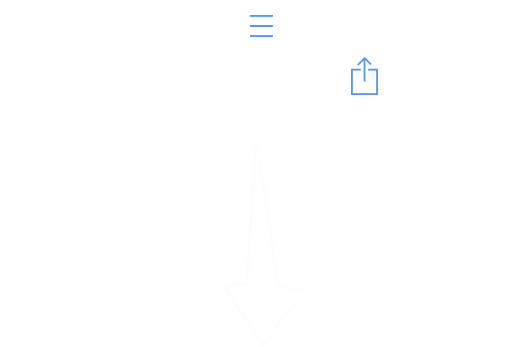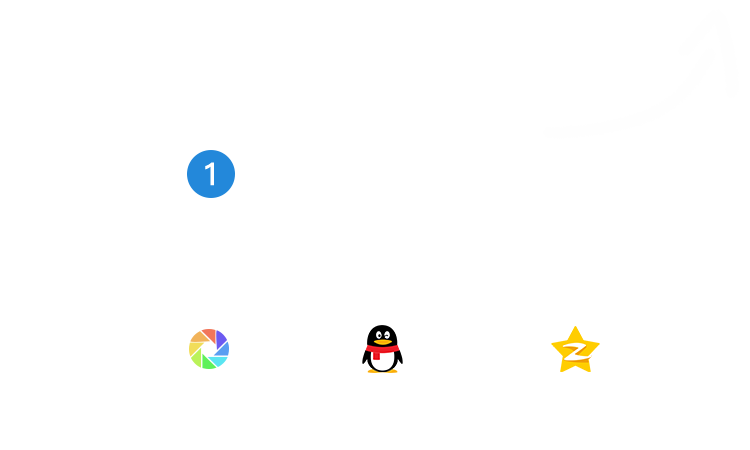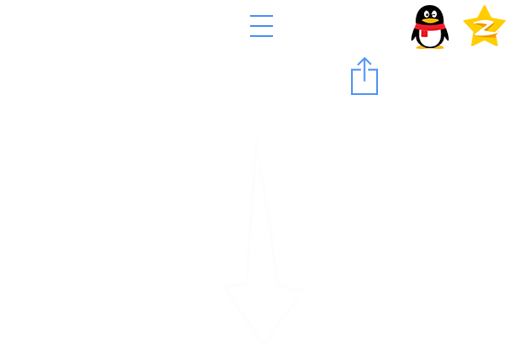唐福珍事件(“黄埔一期”的法科生们)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资料图

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部分学生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资料图

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高校招生改革政策的文章。资料图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1977年冬,改革开放前一年,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
隔年春天,怀揣着录取通知书的姜明安在懵懂中走进了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校门。
这位北大法学院教授、我国行政法泰斗级人物,彼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他起初并不知道,这一年,仅有三所高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了法律专业。
而他和他的83名同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北大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被称为法律界的“黄埔一期”。
40年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逐渐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今在法学领域和涉法公共事务上,都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对中国法治建设影响深远。
忽如一夜春风来
恢复,是一切的开始。
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其时已经26岁的姜明安还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程。
他自小热爱读书,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因“文革”辍学开始,姜明安无论是在务农、当兵,还是在乡下搞工作队围湖造田的日子里,都没有中断过自学。“但那时候从来没奢望有一天还能上大学,毕竟高考都取消了,我也过了岁数。”
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力抓教育。
这一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其实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姜明安压下自己复杂的心情,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负责的两个班百十来名的学生身上,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
不曾想,几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再三确认了老三届都可以参加时,都快高兴死了,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录取通知书是被装进一张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寄来的,收到信的姜明安喜极而泣。
同样一纸信封,也邮到了何勤华的家里。
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如今已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还在工地上挖河泥。
此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再与大学失之交臂。
“那一刻,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我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回了家,开始准备去北京上学的行李。”何勤华回忆道。
一个月后,当从上海出发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也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
这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他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学生们依依话别。
19岁的陶景洲也在路上,背着棉被,从安徽蚌埠上了火车。
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此时,更多的同窗也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4年的聚会。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出生时间分布排列在1946年到1960年的每一年,年长者与年幼者的年龄差距超过一轮,几乎形成代沟。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同时使我们这些年轻者颇为受益。”陶景洲(现美国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说。
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黑皮肤,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这个人正是李克强。
其实高考填报志愿时,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何勤华后来才知道,当时进入北大法律系的这83名学生,志愿几乎都不是法律专业。
刚经历过“文革”,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法律,当时内心对法律专业一片茫然。”何勤华回忆道。
他本想上老家的复旦大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取到北大;陈兴良(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第一志愿也不是法学;陶景洲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郭明瑞(现山东大学民法学教授)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想学美学……
就这样,“黄埔一期”的各路英雄误打误撞地走到了一起。
未名湖畔的求学时光
特殊年代给了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但也给了他们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
陈兴良用“热情”概括了自己最初对北大的印象,“这种热情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经历了动荡坎坷的学生也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图书馆、教室、食堂和宿舍,四点一线之间,都是他们埋头苦读的身影。
“当时读书之投入,同学之间可以为经典著作中的一个概念的理解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陈兴良说,“学校的包容、宽容与纵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每一种兴趣与爱好都可以得以升华。”
同样,老师们由于10年未曾施展,对法学教育积攒了极大的热情。
北大法学系80多位老师,共开20多门课,好课都是口口相传。
最有名的一门是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课,授课老师叫龚祥瑞,上课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无所顾忌。回忆起当时的求学经历,大家不约而同的提起了对77级法科生影响颇深的龚祥瑞老师。
龚祥瑞早年专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治、法治有亲身体会,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
陶景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年逾古稀,却和年轻人一样,充满热血。
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最后也都钻进了龚祥瑞的课堂。
再后来,这群法学青年已不满足于课堂。
许多个读书的下午,他们约着一起去中关园东边的老楼——那是龚祥瑞教授的家。
一个老人,一群青年,一个小庭院,他们从欧美政制和宪法聊到中国的法治进程,直至月明星疏,老人拿出一瓶白酒,学生买来毛豆和花生米。
酒酣人乏,月落西窗,青年们睡得东倒西歪。
当然,困难也不是没有。由于77级的法科生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国家法治尚未恢复。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此后才开始大规模的立法以及司法重建工作。
因此,当时的法学研究可以说是一片废墟:没有专业书可读,甚至连教科书也没有。
“就以刑法为例,我国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7月1日通过的,我们的刑法课是1979年9月开始上的,这时还没有一本刑法教科书,直至我们大学毕业刑法教科书才出版。”陈兴良记得,法律专业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读书吸收精神养分的过程,“都是通过大量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止一遍两遍。”
教材实在太少,大家就尝试着翻译国外法学著作。
姜明安记得,刚刚进入第三学期,他翻译的塔吉沃祥的《再论完善经济立法》和郭明瑞翻译的哈尔斐娜的《完善经济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便发表在了《国外法学》期刊上。
后来,还是学生的李克强还曾修改完善过老师龚祥瑞的文章。
当时,龚祥瑞敏锐地注意到国外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与法律联姻的问题,写完后觉得没说透,就找来英语很好的李克强,让他查些国外文献资料作补充修改。
李克强修改后龚先生很认可,后来将两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
李克强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感慨地写到:“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
“黄埔一期”初出茅庐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大三时姜明安的专业兴趣从经济法转向行政法。
他记得龚祥瑞曾在宪法课上大讲行政法,说行政法是“实践的宪法”,是“动态的宪法”,“没有行政法,宪法只能停留在纸上”。
姜明安被深深触动了。
“我在当兵前,从没吃饱过肚子,妹妹差点在大饥荒中饿死。”大跃进、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就躺在姜明安的记忆里,他忘不了那些受尽苦难的亲人。
“那时,约束、规范政府权力的行政法近乎无人问津。”姜明安解释道。
但现实是,那时我国大学还没有任何一门行政法的相关课程。
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阅读行政法、宪法和公法原理方面的著作,如孟德斯鸠的《法意》、罗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戴雪的《英宪精义》等。
龚祥瑞很是器重和关心姜明安,时不时就会带他去参加法律界的相关会议,并让他参加自己主持的相关课题。
但在临近毕业时,龚祥瑞却对他泼了冷水。
“龚老师对我说,‘姜明安,你可要注意自己的饭碗’。”今天回忆起来,姜明安说,龚祥瑞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当时,行政法依然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和误解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人们谈法学体系时,都将行政法学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
“整个法学教育中,规范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现在国家管理,约束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法所占的比重小得可怜。”姜明安解释道,“龚老师告诉我说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他很担心我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
然而,固执的姜明安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豪气冲天地立下志愿:“不能生根我们就改造土壤!”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
当时83名学生中留校4人:姜明安、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
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名同学,选择出国继续深造。
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杜春进了司法部;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法官。
留校的4人中,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姜明安对自己的工作很是珍惜,尽管他最初的工资还不到100元。
他也曾有机会离开北大。
1984年,中央组织部成立“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现在的公务员法)立法组),还只是助教的姜明安也被邀请参加。
在立法组工作近半年,中组部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曾两次派人到北大协调,要调姜明安去部里任职。
但姜明安拒绝了,只拿了部里给的1000元补助,安心地回到了学校。
如今,他是全班83名同学里,唯一一个始终没有离开北大的人。
走出国门的陶景洲去了法国巴黎,在之后的30年里,为贝纳通、家乐福等几十家国外著名品牌和企业到中国投资提供法律帮助,成为著名的“跨国生意幕后人”。
2008年,他还曾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未名的77”
回国这些年,陶景洲认为自己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代表很多中国企业应对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诉讼。
“既然要和外国做生意,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而且真正要用这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武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陶景洲一直坚守的原则。
如今他把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管理得很好,几项主要的业务领域如国际仲裁、国际兼并收购、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正是他当年想要的“实务为国”。
姜明安也不负初衷。
后来的30年,姜明安除了本职教学工作外,一直在全国人大等立法机构参与着“改造土壤”的立法工作。他曾参与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要行政法立法研究和试拟稿起草工作……
但他第一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因为一起自焚事件。
2009年11月,因为自家投资700多万元的综合楼只获得了217万元的拆迁补偿款,成都市金牛村47岁的农妇唐福珍在拆迁队员面前选择了自焚。
一个月后,以姜明安为首的5名北大教授以公民身份,通过特快专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部分条款。
“北大五教授建言全国人大”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姜明安说,层出不穷的“血拆事件”把他刺痛了,觉得不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心里会不安。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同时宣布老的“拆迁条例”废止。
这是姜明安最欣慰的一个回应。“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只是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
此后,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草拟行政程序法。“现在,我国的行政法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就完整的行政法体系而言,我国还缺少一部基本的主干法律,这就是行政程序法。”
2015年10月1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报告厅,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发布了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
这部法律,从首次提出到现在已近30年,一直没能出台。
30年,几乎耗掉了姜明安的半生。
“你能想象吗,行政法这三个字,在这30年里,我几乎天天要说。”但他又很有耐心,“我现在还不到70岁,等5年、10年,等到我80岁总能看到吧。”
为了不留遗憾,姜明安至今仍在积极推动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而同时,他的同学也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前程,罗豪才离开北大后任职于部委,后至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克强则在1982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常委,如今成为国家总理。而其他同学有的成为了著名法学家,有些在各省高级法院、检察院任职,也有的做了大学校长和法学院的院长……
偶尔,他们会怀念起几十年前的求学时光。
姜明安说:“每当想大家的时候,我就会翻翻老照片,翻翻‘未名的77’。”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