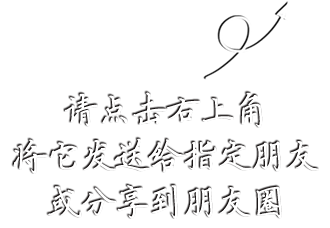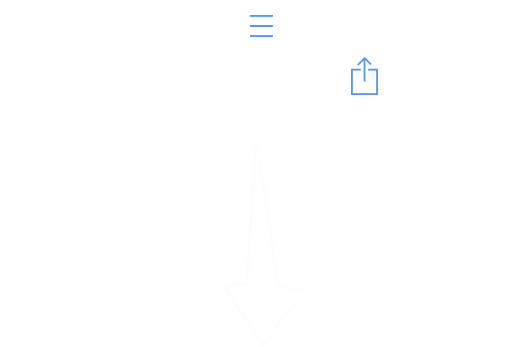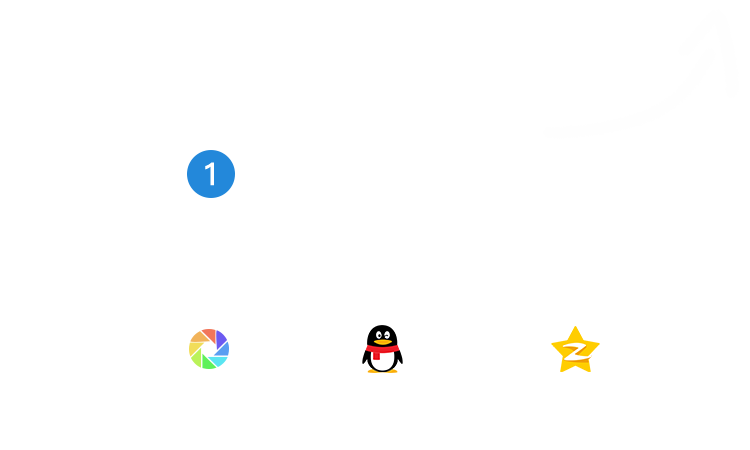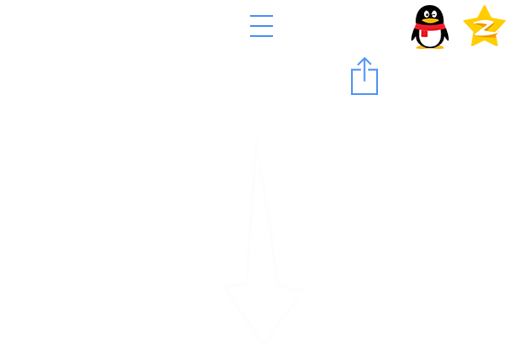采访对象:郭大江,男,三十七岁,司机,
离婚关键词:出卖自己
离婚指数:***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开出租车的朋友认识了郭大江,这个人的面相更奇怪,他长着一张刀条脸,眼睛一大一小且对比强烈,无论白天黑天,面色总是灰青,全身散发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阴郁气息,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我那个开出租车的朋友后来火了起来,他脑子灵活,用开出租赚的钱买了几台二手的解放车跑运输,后来发展成了一个车队,于是他的买卖做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九三年,这种跑运输的车队很紧俏。
郭大江作为老乡开始进入我朋友的车队里,后来就在他浮沉起落的时候一刻也没有离开他。那个车队因为几次大的人命事故最后解散了,但我的朋友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后来远走东北,开了一个特大的药店,成了千万富翁,而郭大江,就成了他的司机。
也就在那时,我的朋友离了婚,至于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另一篇故事里的素材。不是这里要说的,这里要说的,是我在采访朋友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的郭大江的故事。而对他的采访,是通过我的朋友介绍的,朋友说:我的故事与大江比起来差多了,他的故事才好看,精彩,辛酸,而有劲。
朋友还说,你不要看大江一脸晦气相,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有过让我们最羡慕的幸福时光,可惜,这样的时光,再也没有了。
可是,他会接受我的采访吗?我猜测地问。
会的,他一直想找人倾诉,可是没有合适的人,如果真的有人肯听他说,他又对这个人不反感,他会说得很多。朋友肯定地说。
我一直在找我的老婆,我知道,今生搁哪儿旮旯再也找不到那样的老婆了。我老婆叫蔡玉芬,村里人都叫她芬子。芬子和俺好的那年,才十四岁。
我是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生的,可是后来在沙河子长大。我爷爷家在那,我是爷奶一手带大的。鸡西那个地方是产煤的地方,我长大后就在矿上,你别看我瘦,可是我有的是劲儿,干力气活可是把好手。芬子她老家在沙河子,每到周六周日,她就从沙河子坐车来看我。
她那小样儿,我永远也记得。她总是穿一件花棉袄,戴个小白围巾,远远一看,像个小绵羊,让人爱死了。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在沙河子庄南,她在北,从我家到她家,二里地不到。芬子起小就泼辣,假小子样儿,我们秃小子玩儿什么,她玩儿什么,上山采酸枣,每次她都是采得最多,打架,上树,赛跑,她也样样不输。她妈教她女工活,她不学,气得她妈老骂她,说她嫁不出去。
她十四岁那年,我和芬子在秃顶子山拜了天地,后来我们就经常去那儿,我比她大一岁,那年我十五岁。小屁孩懂什么情啊的爱啊的,就是大家总在一起,有个玩伴儿就是了。不过芬子有算计,她说她就跟定我了,我老家在鸡西的矿上,将来我长大了一定会在矿上做工,芬子说她将来要嫁就嫁城里的人,嫁做工的人,不和那些与黄土为伴的过日子。
芬子十七岁那年,出落得出息了,不是个假小子了。她留一条大辫子,油亮乌黑,一甩一阵风,那脸也由紫膛色变白了,胸也挺,她们那村,还真没有几个她这样的。芬子的性格也变了,不那么泼了。爱笑,但不是以前那样嘎嘎地笑了。村里的人都说,芬子变回丫头了。
我和芬子她妈提亲,是在我十八岁那年,她妈没干。因为她妈早就给芬子相中了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民办教师,到这里来就是过渡一下,捞点资本,将来回城的。芬子她妈看中了他的学历,听说是什么大专学历,将来能在城里发展,我不过是初中,肯定一辈子要在矿上混了,芬子她妈是农民,可是对我们矿上的人还是有偏见。
她妈不同意我们好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刚顶替我爸上班,我爸在一次塌方时砸碎了脚踝骨,再也站不起来了,家里就有了个瘫子,我妈身体不好,脑血栓多少年了,家里还有个二弟,才上高一,摆明了,谁过去谁就得侍候瘫子,哪家的姑娘愿意一过门就侍候人,芬子她妈也是因为我家这条件,不让她和我好的。
可是芬子不这么想,我和芬子,套句文话来说,也是青梅竹马吧。小学俺俩一块儿上的,初中一块儿上的,秃顶子山俺俩也一起爬了不知多少回。俺俩是有话说的,不怕你笑话,在大队的谷子场后面,俺俩第一次亲嘴才十六岁,那个感觉,以后再和别人可找不着了。
芬子她舍不得俺,俺也舍不得她。但她妈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我买了两瓶沙河王,托人带了一条红梅烟,让我老叔拿着和她妈说了小半天,也没说服她妈。我那时是灰心了。爸来信催,让我回单位去报到。没办法,走吧。
走的那天赶上个大阴天,心情也灰。没精打采地走着,心烦,到了秃顶子上绕一绕,就看见芬子了,芬子问我:咋的?我说:完了,烟酒都拿回来了,你妈不干。芬子就笑了,
说:天地都拜了,她不干也得干!我问:你有啥法儿?她说:把生米做成熟饭不就得了!
芬子是有主意的,在这上比我有主意。那天她和我定了个计,说出来也真让人笑话。芬子不知从哪本书看的,说女人一不来好事,就是有那个。回家她就和她妈说,她有那个了。
我当时十九岁,什么也不懂,女人的那好事是什么也不知道,芬子托我叔帮忙,从城里开了一个什么诊断证明,我叔说,那个什么证明上能证明芬子有了,那个证明不是芬子的,鬼知道是谁的,不过,这个证明的效果挺好,芬子她妈过两天就松口了,要我叔来,把这事再商量一下。
芬子真有办法!我当时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妈后来知道上当了,不过那时村里都知道她已经接了我家的定礼,这事是芬子自己说出去的,她妈想反悔也反不了了。
我和芬子那天晚上在秃顶子山上看月亮,芬子说起骗她妈这事,笑个不停,我搂着她,她那时有点胖的,全身肉,摸着挺舒服。我逗她,我说生米这次可以真成熟饭了。她说,敢。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敢了,芬子有主意,也敢干,这点比我强。我俩搂一块儿亲热半天,最后也没成熟饭,后来看月亮都圆了才回去。
我和芬子是骗人后才在一起的,这个事,多少年以后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我后来到矿里上班,芬子常常到城里来找我。鸡西也不大,有时她在我宿舍住一天,我们俩绕着矿上走一圈,有时走得远了,就到街上去了。我那时刚上班,但工资也不少了,一个月有二百多块,在俺们那,这钱也能买不少东西,我有次带芬子上街,问她要什么,那商场里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芬子就看中了一个白围巾,那是手工织的,上面还有
两只蝴蝶,那围巾也不贵,才三块多钱,我说我给你买点儿好的吧,可她就要那个,后来她就总系着围巾找我。
我们那时候都特纯,有时芬子在我们那里住一晚,我搂着她睡过,可是没想起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我们认为这样就挺好了,还要做什么呢?
芬子正式嫁给我是在半年后,我在矿厂转了正,正式娶她是在一九八七年,我是到沙河娶的她,那天租了一个面包车,就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把她娶来了。我准备了一万块钱,那是我爸打工赚下的,作为彩礼给了芬子她妈,那时一万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芬子知道我家有个瘫子要治病缺钱,还有个弟弟要上学,后来又从她妈那要回了七千多元,这事我也一直挺感激她的。
我和芬子在鸡西生活了三年,我们没想过要小孩。关键是要了也没地方住,我们和我爸住在一起,一共四十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我和芬子住一间,我爸妈就住另一间。我弟弟在地上打个铺睡,那时住房太紧张,我是个新工人,也分不上房子,要个孩子,放哪儿?
我在矿里,每天干的是卸车的活,挺累,那时一回家,芬子就烧一大盆水等我,水很热,芬子很爱干净,她说不洗干净不能上她的床,女人就是多事,不过洗个热水澡也真是舒服,我后来习惯了。我以前都是拿凉水胡乱一洗就完事,可是现在要是一天不洗个热水澡,还真是受不了。芬子后来不在我身边了,可是这习惯却也改不了了。
那时的生活,淡淡的,但是挺自在。芬子后来也到了矿上,在劳务队做临时工,主要是扫马路,干点杂活。我们俩口子结婚头三年,好得什么似的,从没拌过嘴。
芬子是个好女人,她懂事,勤快,嘴也甜,矿上的人都喜欢她,我爸妈也喜欢她,芬子还会做饭,特别是做鱼做得拿手,我是个拙嘴笨舌的人,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有数。
一九九一年,我当了副工长,应该很忙,可是却没活干了。那年煤炭市场紧缩,全国的煤都不好走。我们的厂子也不行了。后来开始下岗裁人,但是也没起多大作用。那一年,整个黑龙江都不好整,何况一个鸡西矿,我知道情况不妙,但没想到来得那么快,有天早上一上班,主任就通知我,矿上要裁下五百人,我也下岗了。
我哭了,你知道,我爸在矿上干了一辈子,可是到我这却失业了。我能不委屈吗?失业了干什么去,我还没想过呢。我当时想得也比较天真,我以为要是下岗,怎么也轮不到我才对,我身壮力强,怎么也能干个十年二十年的。我哭了,一个大男人哭起来挺丢脸的,我没敢在家人那哭。我一个人来到外面,在风中哭了起来,那天下着大雪,特别冷,一会儿泪就在脸上冻成冰了。
不知哭了多久,一回头,芬子就在我后头站着,哭啥,她说。去沈阳吧,找你老叔,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知道我老叔在沈阳,他是个木工,在一个装修队里搞装修。我小时候和老叔学过几年木工,可是这几年没整,都忘光了。芬子说的这个也是个法儿,沈阳那边是个大城市,搞装修还是有点搞头的。可是我行吗?我说,我可扔了多少年了。
你一个大老爷们咋整成这样了,芬子用手戳我额头,矿上那活就好哇,一身黑,一身汗的,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和她犟,我说那也是个皇粮。她说:屁!什么皇粮,能吃一辈子,我给你放了热水,你先洗一洗再说吧。
我那天泡在盆里,芬子给我搓背,我一边洗一边想,芬子的话是对的,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成让个工作给愁死。我家里也没什么可愁的,我爸一年前去世了,弟也上班了,就老母一个人。我们两口子合计合计,给老叔打了电话。老叔那头还真缺人呢,他在的那个
装修地也是个大公司。于是,我决定马上去沈阳,芬子也和我一起去。
俺俩收拾行头,把这几年攒的钱留一半给了家里,另一半芬子给我缝在了腰带上,带着一个大包,就坐上去沈阳的火车,我们那时都年轻,虽然不知道沈阳会不会有更好的生活,可是心里还是有念想的。但送别的那一刻,心情也不好过,芬子靠我肩上,我们从车窗外看二弟和妈在向我们挥手,车开了,他们的身子越来越小,二弟长大了,都有胡子了,妈更老了,头发全白了,站在风中身子老是抖,她的脑血栓也比以前严重了。我想起爸,去年心脏病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干了一辈子的那个厂子已经完了,我哭了。芬子搂着我的肩膀说,别哭,到了沈阳,好好干,接他们来享福。
我们到沈阳时已经是晚上了,我叔在车站接我们,我小时候来过沈阳一次,长大了就很少来,虽然这里离黑龙江也不是很远,可是芬子很少出门,她还是头一次来。沈阳可真大呀,我老叔带我们去他住的地,坐公交车坐了十几站地还没到,不过,芬子可高兴了,她在车里东问西问,问这是哪儿那是哪儿,我老叔就是笑。
我老叔让我先住他那,也不过就是一间房,没暖气,得生炉子,我老叔已经买了足够的蜂窝煤,点上后屋一下子就暖了。芬子乐了,她说,可惜你家的那个大盆没带,要不我又可以给你烧水洗澡了,我老叔乐了,说:傻孩子,那得多少煤,不如去公共浴池划算。
我们到这第二天,我老叔领我去见他们装修公司的头,把这事定下来,我给老叔他们打下手。那头问我,是不是成手,老叔一口应承下来,说没问题,我知道我得快点学,不能给老叔丢人。老叔说芬子的事不太好办,但他以前给一个开饭店的老板装过修,处得不错,他那也是个大饭店,他可以去找他说说,让芬子先去那做服务生。
老叔那天晚上要请我们吃饭,可是临时因为一个收尾不利索的活又把他叫去了。我把芬子接出来,两人来到了一个饺子馆吃了饺子,我告诉芬子,说我的事已经定了,过几天就可以开工了。芬子两眼放光,要了酒。我俩喝了几杯,突然想起,今天还是我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芬子说这个纪念日也挺有意思,是在沈阳过的,而且这一天还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我问芬子,想要我送给她一些什么?芬子想了想,说她还没去过故宫呢,她想看看故宫。
那天晚上已经快九点了,我借着酒劲,来了情绪,说这有什么难的,咱们走!我们打着车来到故宫,早就关门了。不过,从门外看,故宫也挺雄伟的,虽然都是黑压压的房子,可是又高又大,看着也让我和芬子眼都发直了。芬子说:妈呀,一个人住这大房子,什么时候咱们才有这样的一间就行了。我说没问题,芬子,你看我的吧。我俩那天沿着故宫的路边走边谈,后来迷了路,可是也不害怕。
沈阳好像比鸡西要冷,可是我们越走却越热,走着走着,看见一个立交桥,挺长挺亮的,一排排全是路灯。芬子说,大江咱们回不去家了,我也走不动了,怎么办?我说,走不动我背你,我背你回家!芬子说:大江,咱们今天就结婚四年了,四年了,我除了那条围巾从来没有给你要过什么,我今天想要你做一件事,我要你背着我,从这个立交桥走一圈,再走回来,让我好好看看沈阳的夜景,好吗?我说好。
于是就背着芬子,往立交桥上走,那桥很长的,可是灯也很亮,芬子说她能把我后脖梗子上的汗珠子全数清楚呢。芬子有点胖,我走到一半就有点走不动了,可是我还是要走下去,因为我答应了她。
我们走到桥中间,离地面有几十米了,芬子说:大江,你停一停吧。我要从这里好好看一看沈阳。我们就停在那里了,风很大,一吹,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寒战,汗全没了。沈阳就在脚下,芬子突然大喊一声:沈阳,俺们来了!
我的泪流了下来,那一晚,我背着芬子在立交桥上走了十个来回,我以为我是最幸福的,却不知道,到了沈阳,未来其实是一抹黑的。
我在沈阳一共干了两年,赚了一些钱,但是后来又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把我两年来赚的钱都倒光了,我借了我老叔五千块钱,要不,一条命就交待在沈阳了。
我们在沈阳租了房,芬子也在一家饭店打工,她嘴甜,能干,后来就在那个饭店当了总管。我病了的时候,她为了照顾我,把工作也辞了。我整整住了两个多月的
医院,罪遭老了。可是还好,我又挺过来了。
我好了以后,原本以为可以好好干一场,把借老叔的钱还上。可是沈阳后来比鸡西还惨,好像一夜之间,下岗职工就满大街都是。破产,失业,那一阵子,大马路上响的都是这些声音。市政府门口天天有人上访示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市场可说。我老叔的那个装修公司也完了。我也失业了。芬子后来又回到那家饭店去了,可是生意也不好。我们又陷入困境了,而这次,比在鸡西还惨,我们还有债呢。
我找不着工作,老叔那时也不时地敲我,说他现在也不好干,意思就是催我还钱,只不过不好意思说。每天愁得不知怎么才好,一个在找工作时认识的老乡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去北京,说他有个朋友在那做贸易,主要是捣腾黄豆,现在缺两个能来回跑的业务员,月薪八百,工资还不低,但平时要在北京办公,有业务了两地跑,比较辛苦。
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工作都得干,还在乎辛苦。我应了他。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芬子告别,我说等那边一安顿,我看有法子就接她。芬子哭了,俺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一直是一起进退的,这一次我要一个人走,她不放心也舍不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和老乡一人提了一个行李,上了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为了省钱,买的是站票。那天的车正好赶上大学生放假,人多得连喘口气都费劲,这一路上,那罪遭得也可想而知了。不过,一想北京可能有发展,我俩啥苦也都能吃了。
到了北京站,也不过六点多呢。那是冬天,天黑得早。我下了车,想方便一下,解个手。火车上人多,连厕所都挤满了人,这一路上没去了几回。下了车,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候车室找厕所。我把行李都交给老乡了。就一个人去了候车室的厕所。
那天北京站的人太多了,北京站也太大了。我从厕所出来,正好赶上又一列车进站,人呼地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而那些拉人住旅馆的人也冲了上来,我一下就被人群包围了,好几个人把我拦住,问我住不住旅馆,我当时就懵了,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哪见过这么多人,哪见过这么大阵势,那几个人不依不饶地跟着我,好不容易冲破人群的包围,等冲出来时,天黑漆漆地找不着刚才和老乡呆的地方了,这一通找哇!等好不容易找着了,那儿已经没人了。
这可坏了,我的行李还在他那儿,里面有被子,五百元钱,和一些生活日用品,他突然没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联系上了。我急得满脸汗,满火车站地找他,可是找不见。后来又到列车问讯处,人家也说,没人来找过我。
我的脑子一下子大了,我说什么也不相信,我的老乡会摆我一道!东北人,最实在啦,他怎么能摆我一道呢!我继续找哇找,最后车站都没人了,也没找着他,我后来就扯着嗓子大声吼起来,喊他的名字,可是没人答应。后来列车上的乘警来了,问我什么情况?我把事跟他说了,那乘警不错,用大喇叭在火车站广播了一下,可是他还是没有出现。
快十二点了,我找不着他,终于相信再也找不着他了。我蹲在火车站广场的一个马路沿上,呜呜地哭了,哭出来我的心头才会舒服点,不这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走的时候芬子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里面还装着三百元钱和身份证。我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钱和证件取出来。搭了一辆
出租车,找着一间地下室,四个人一屋,一晚上每个人四十元,先住下再说吧。
我在北京给芬子的饭店挂电话,她还没下班。我说我到了北京了,挺好的,住下了,让她别牵挂,明天一早就去见工,等稳定了再给她打电话,我没敢和她说发生了什么事,我怕她着急上火。
我身上就那么点儿钱,根本就挺不了几天。我和那个东北老乡也不过是认识没几天,没他的联系方式,也没给他要过我们要去的那家公司的电话和地址,我找不到我们要打工的那个地方。再说,也没那个时间找,我得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满大街地到处打听哪里缺人。不到北京不知道,这里外地人竟然有那么多,而找工作的人更是多得吓人。
我在一家小饭店里绕,说自己会做墩上的活,那老板问我一月多少钱肯干,我咬了咬牙大着胆子说五百,老板摇头,我又降到了四百,老板有些动心,我刚要说三百也行,这时门口就挤进了个人,说只要管他吃住他可以白干,老板当即就拍板要他了,这种情况,我还能说什么。
在北京绕了一天,坐车的钱花了十几块,走了几十里路,可是一份工作也没找着。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找不着相熟的老乡,哪能那么好找工作的。饿了一天,在门口买个馒头,这就是一天的饭了。
在北京呆了几天,我身上就剩下三十块钱了,没办法,再找不着工作就要要饭去了。后来还不错,住的店里找着一个老乡,问我愿不愿意去工地上干,管吃管住,就是离得远点,在昌平,我说行。老乡说,干不能白干,得交点抵押金,先交二百元才能上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中介费,是给他的,根本要不回来的,那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答应了他。还签了协议。他给我开了张收据,说让我先干着,什么时候把钱给他,什么时候把这收据给我。
我们十几个人被一趟车拉到了昌平,住的是大通铺,顿顿吃的是白菜。我们到那去,主要工作是打桩,这是一非常累和苦的活,但是工资不低,干得好的话,一个月也能收个千八百的,我就应了,晚上给芬子打电话,说我找着工作了,可是人家要先交押金,让她给我寄点钱过来,先寄五百。我听见芬子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好像说了句:你老叔刚才来了才走。我知道她也难,可是我在北京已经快完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了,我说你想办法把钱寄来吧,我需要呢。
放下电话,老乡来约我喝酒,说他把钱先垫上了,让我好好干,会有希望的,我谢了他,那天晚上,觉睡得才香呢。
我在工地上干了三周,是试用期。累得险些吐血,但好在我干活还算踏实,就留了我。
我在这儿一干就是多半年,后来因为太累,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是哮喘病的底,一发起病来,上不来气。天冷,再住在大通铺是不行的。我就和别人在外面租了间房住,这一租房子再加上吃的费用,一个月的钱剩不下几个,芬子开始几个月给我寄过钱,后来我勒紧肚皮,不让她寄了,再往后,我的生活好一点,就是我给他寄了。
北京这个地方,其实找工作比沈阳好找得多,我刚来的时候,一个熟人没有,所以才吃了很多苦,后来认识了几个老乡,通过他们的引见,我又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搞运输的公司拉货跑长途,我在北京学了开车,就到那儿上班去了。这回好了,不但活轻松了许多,最关键的是可以回沈阳了。因为那个公司主要和东北那边有贸易,我的工作是两头跑,可以时时回沈阳住了。
我在半年来,和芬子始终写信和电话联系。后来芬子说北京长途太贵,让我没事别打电话了,写信吧。我们通了几次信,芬子让我安心干,说她在那边生活得还可以,我老叔的钱正在慢慢还,快还清了。
半年来第一次回沈阳,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虽然沈阳不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和芬子在这里曾经真正地度过了两人的世界,这已经成了我的家了。我开着解放一路飞奔,到家门口心就跳,我想芬子会是什么样,还是那小白围巾红棉袄吗?
芬子在家等我,我回家时她正在家里给我炒菜,我一进门就搂住了她,俺俩都哭了。芬子还是芬子,但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她比以前瘦了,脸颊很瘦,精神也不大好,脸色特白。芬子喜欢穿素的,可是现在她却穿得很艳,还穿了一双红鞋,这鞋可是我以前没看过的。
看我回来,老实说芬子没有我想像得那么狂喜,咋看出来的?我一回来,搂着她就亲嘴,可是她居然推了我一下,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俺俩可没少干过这事。吃完饭,我搂着她办事,她又推三阻四,说今天不行,不舒服。真扫兴。
我们俩开始说起分手后的这些事,我把北京的事都和她说了。又问她怎么样,芬子说老叔的钱已经还清了,她还在那间饭店工作,只不过,那个饭店已经改成夜总会了,她天天上夜班,管收款,虽然辛苦,但是收入还不低。说着说着,芬子身上有响动,她迟疑了一会儿,拿出个小手机来,接了个电话,啊了几声。我说芬子你什么时候有这个了,芬子说,是老板的,她拿着呢,工作用的。
芬子和我呆到了快九点,那电话又来了一次,芬子说不行了,她要上班了,我有点不高兴,说我可是刚回来。芬子说她也知道挺对不起我的,可是这的工作就这样的,不能替班,她让我先睡下,说明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她了。
回来几天,芬子天天晚上去上班,而早上一回来,就无精打采,困得直想睡觉。我觉得有点不对劲,芬子以前是爱说爱笑的,让她这么着不说话,那可是个难事,她怎么了?我问她,她说熬夜熬的,睡睡就好,可是她这一睡,有时下午才醒,到晚间又出去了。
我回来这一次,觉得芬子变了,说来不怕人笑话。在外边一去半年,女人就没沾过,人说小别胜新婚,我回来攒足了劲,想和媳妇好好热乎热乎,可是芬子总是说身上来好事了,不舒服。我愣是一下也没碰过她,这还算夫妻吗?
有的时候,我还在芬子身上闻过烟味,我问她怎么回事?芬子说他们那个地方,有几个男服务生抽烟很凶,沾到她身上的。后来我发现她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对,她也抽。我有一天在家里的地上捡到个烟盒,我问她是谁的?她说是她的,我问她怎么学会抽烟了,她说是想我想的,想我时,就抽根烟,心就不烦了。我对这个说法很怀疑,而芬子从那天开始,就干脆明目张胆地抽烟了,她的烟抽得还很凶。一天一包,烟也不错,是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