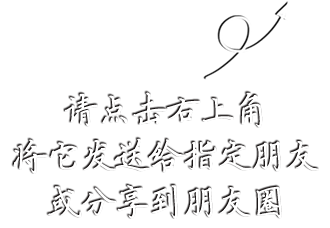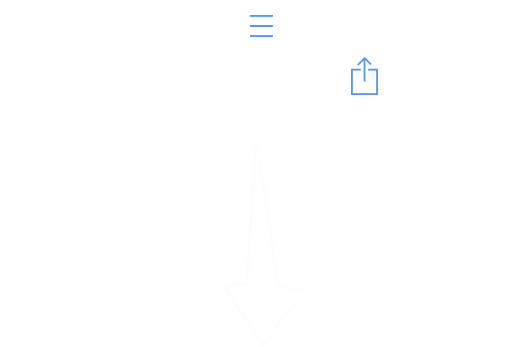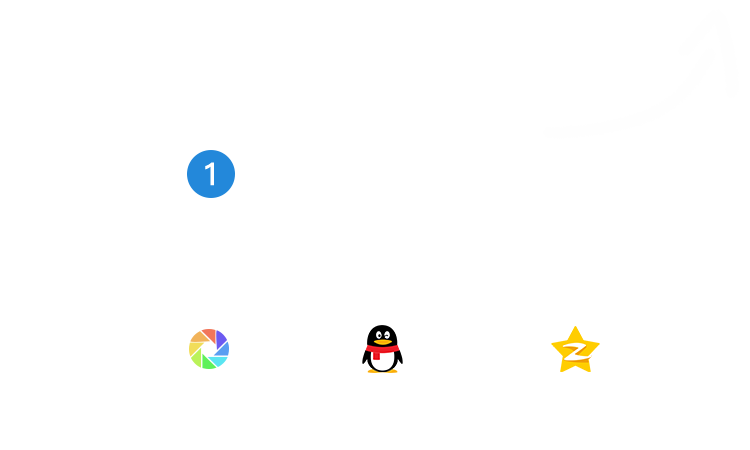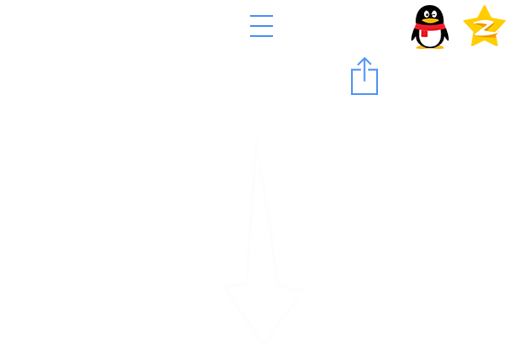“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读过这期“我的故事”,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辛弃疾的这首词。人生百种况味,在字词游转间,跃然纸上。
企业家不是诗人,没有细腻婉转的文字,然而回忆起当年的第一份工作,却都有着一种百转千回的洒脱。
谁都有过年少无知,谁都有过书生意气,然而岁月磨练,时光蹉跎,磨圆了人生的棱角,人生起步不容易,但在少年却没有那么看重选择,似乎时间多得是,明天定能拼出个天地。第一份工作与成功有关,也可能无关。
不知道巴菲特在15岁时,在他父亲的股票经纪公司的黑板上抄写股价是不是注定了这位“股神”的未来;不知道默多克当年在伯明翰的《公报》上开辟的小专栏,是不是开创了新闻集团的先声;也不知道丰田喜一郎担任机械师时是不是就想到了要开创世界第一的汽车帝国。他们的起步与未来的成功或多或少有点关联,世事总是在潜移默化中烙印着人生。
也有人的第一份工作与未来毫无干系。谁能想到日本佳能公司的开创者之一御手洗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北海道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助手;又有谁能想到台湾商界巨擘王永庆最初只是个茶楼跑堂;人们恐怕也不会知道戴尔公司的创立者迈克。戴尔的第一份工作和中国还有点关系,他还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当过小工。正如本期讲述中的一位企业家所说,人生重要的不是在起步,而是在转折。未来的掌控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说了这么多名人轶事,其实“第一份工作”不是在猎奇,而是在寻找一种共鸣。有人说,第一份工作就像初恋,或许有的苦涩,有的幸福,在反复寻找中总是,“欲说还休。”
当年的“混世魔王”
口述。北京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阎焱
究竟什么该算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也说不清。如果说第一份拿到工资的工作,那应该是排球运动员;如果说第一份劳累的工作,那是插队下乡,做农民;如果说每天八小时上班的工作,那恐怕是在飞机仪表制造厂做工人;如果说在美国生活,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世界银行上班。但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做投资。
做排球运动员,恐怕纯粹出于一种爱好。那时十六七岁的我,正值青春年华,在大院里,我们家五个男孩,各个痞得要命。我在家排行老大,也就成了这些“混世魔王”的老大,天天打架。可是后来喜欢上了排球,要打排球,家里全力支持,因为打排球就不用打架了。
到安徽省队,我净跳能达到97厘米,教练看是个苗子,就把我招了进来。那时候正值“文革”,我觉得能有一份球打,不用下乡,真的是一份很不错的差事。而且在排球队,待遇好,有牛奶喝,更是美得不行。当时根本没觉得训练有多苦,全国各地打比赛,团队生活真的很带劲。现在想来,无论运动或者别的什么职业,只要你投入进去了,就能欣赏到其中的美。
虽然打球很愉快,但我还是想上工农兵大学,可是打排球上不了大学,于是我还是下了乡。下乡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感受,开始的时候挺高兴,后来就是绝望。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生活上的艰苦,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你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但把你扔在那个穷乡僻壤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前面一片黑暗。
终于熬到有资格上工农兵大学了,可是“文革”结束了,工农兵大学取消,又恢复高考了。一直打排球的我,那时哪里认真学习过,于是翻出来一本老的复习课本,开始复习高考。
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我从小就对飞机着迷,总是把钱省下来去买一本叫《航空知识》的杂志,当时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因为老看书就特想像美国莱特兄弟那样一飞冲天,想想人可以像大鹏一样在天上飞那可多伟大,所以特想当飞行员。1977年,我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被分进当时三机部下属的一家工厂。真失望,本来想驾驶飞机,结果只学了制造飞机,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培养了我对数量的敏锐。
那时候中国的工厂真落后,工厂里有一批聪明的人,可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干活,看报纸喝茶,然后就是骂社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那时候工厂的真实写照。那时的航空制造厂,还真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可惜最后大都废掉了。
我就打定主意要摆脱这一切,在中国想改变一切就要当官,要当官就要上北大,还要学社会学,可是考上北大社会学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北大没呆多久就出国了。毕业后,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银行,这是我经历过最差劲的工作,比中国的工厂工作还无聊。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老让我重复做同样的事,我肯定干不了。做投资,每天我就想着去上班,到办公室,看到小公司长大,给很多人带来就业机会,我就觉得幸福。
我的代号201
口述。盛禹铭集团公司董事长张醒生
每天8小时戴着耳机,不停地与各种人对话,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早上出操,晚上点名,吃大餐,10个人一盆菜,睡大屋,80个人一个房间……那时候,我是一名接线员,但在线路另一端的人不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只知道我的代号——201.
那个年代的电信局还属于军管单位,按照党的指令,一批老人被撤掉,一批学生就被招进来。刚刚从北京125中学毕业的我就直接被分配北京长途电信局,开始了接线员的生活。15岁的年纪,无所谓选择,只知道被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上就要努力去把什么做好。
战备值班、坚守岗位、敌机、警报……这些关键词,组成了我年轻的接线员生涯无法磨灭的记忆。战备值班是24小时不能睡觉,要随时警惕美军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即便我方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阻止敌机,每次紧急警报的上报也丝毫不能含糊。
那是一天清晨6点多,正是最困的黎明时分,许久未眠的我抵不住阵阵睡意的侵袭,耷拉着脑袋,隐隐约约似乎听到有警报响起,却怎么也睁不开沉重的眼皮,迷迷糊糊中便忘记了上报。直到保卫处派人来找我,问我今天早上是不是贻误了一个上空,也就是漏报了一个紧急警报,我才恍若惊梦,想起当时的确曾经听到紧急警报的声音,说是敌军的飞机已经进入到山东半岛这一带了……被吓的不知所措的我只得承认是自己打盹贻误了上空。
按理说出现这样的失误是要被处分的,好在当年我有过立功表现,曾经想方设法通过沿途的铁路站接通了火车上的电话,使单位得以紧急救助了他们出差在外的同事,事后该单位还敲锣打鼓给我们送来表扬信。本来那年要评我当五好代表的,可偏偏后来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失误,最后领导研究决定,既不算我立功也不给我处罚,功过相抵,以通报批评和写检查的形式做了了结。
如今回忆起来,似乎当年有好几次意外皆是由睡觉引发,如果说上述事件让我备受打击,抬不起头,在那个倡导学习英雄的年代感觉到自己的前途受到了威胁,那么另一起“睡觉事件”则是我受过的最大委屈。不同的是,这次睡觉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
一天早晨,几个男生赖在床上睡懒觉,不想上班,就有意让别的同学把他们从房门外锁上。等到被领导发现,来叫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借口别人使坏,把他们锁在里面出不去。偏巧有人看到我最后一个从宿舍里出来,就怀疑是我把那一大帮人锁在屋子里,不让他们上班。于是,领导便把我叫去谈话。十几岁的男孩,当时只觉得是天大的委屈,眼泪夺眶而出,向领导申述自己的委屈,自己明明是好意去叫他们上班,结果却被人冤枉……后来,领导把被锁在房间里的男孩一个一个叫出来单独问,终于有人经不住领导的盘问,报告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锁门的是另外一个男生……
几年以后,自己也成了领导,就会特别注意,不要伤别人的心。因为我理解那种感受。经过岁月的沉淀,四年的接线员生涯留给我的更是受用一生的财富。接线其实是一种交流,我必须学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必须做到既让电话这边的首长不着急,同时又能让电话那边的接线员迅速接通线路。是那段日子,让我学会“听话听音”,理解不同的声音,也给自己带来不同的帮助。
在我19岁那年,由于表现较好,我被单位选派推送到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去学习有线通信。或许,在我当初第一次跨进北京长话大楼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我今生与电信事业的缘分。再后来,我喜欢上了收藏电话,我的藏品里有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电话。有时候我会想,我所收藏的,也许不仅仅是电话,那上面承载的,还有我青春时代的记忆。
与领导斗其乐无穷
口述。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
读研究生时,我就很能写,三年先后发表了25篇论文。那时候,政府机关领导选秘书,就爱挑特别能写的,所以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家司法部办公厅调研处给领导写报告。
从1988年到1992年,我在机关工作了将近5年。我觉得机关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另一个江湖,它有它的规矩,什么事该怎么做,要求很严格。比如,机关里讲究森严的上下等级,而在大学,同学之间是平等的,包括和老师也没什么不平等。其实,这倒不是我遇到的大问题。真正让我觉得压抑的地方是,在学校里比较讲究创新,而在机关里,领导不需要你创新,上面的大领导讲什么,你照着大葫芦画一小瓢就得了。刚去的时候,我总琢磨着给领导写些出彩的好东西,结果反被领导狠批了一顿,说:你看看你写了些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依据吗?这话总理说过吗?政法委书记说过吗?
后来,我就总结经验,把领导的讲话、报告做成一个模版,每次改个主题词就得了,不用动脑子。比如,领导讲过沿海开放战略,现在说经济要治理整顿,我就把模版中的“沿海开放战略”统一改成“经济要治理整顿”就完了,根本不用加什么思想。
到机关之前,我还曾想过以后吃官饭,但进了机关,这样的想法就消失了。因为一旦有我看到不对的地方,我就给领导提意见,所以跟领导干架是常有的事。有时候领导说报告应该改成这样,我就会反驳说改成这样没道理的。
领导有时也会妥协,因为领导经常在《求是》、《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都证明我改的是对的。领导的政治意识很强,当时政治环境也要求讲点创新,得有点新东西出来,领导害怕拿不准新东西会犯错误,可我老写这些,很有感觉,知道什么事说成什么样不会犯错误。
但机关里面从来都是领导批成什么样,下面人就是什么样,哪还反过去跟领导争论好不好的。可对我来说没什么禁忌。所以,我认为是错的,我就照说,蛮痛快的。结果,机关里很多干部都说:“哎,那个袁岳可厉害了,部长都怕他呢。”
我就认定一点,机关里面最重要就是要做正确的事,就是说对的话。不要以为你是部长,你就可以不跟我讨论了,更不用说处长了。我们副处长总跟我说:“袁岳啊,你为什么顶撞部长啊?”我说:“那是部长错了啊,领导有不对的地方,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他进步?”我们那副处长说:“领导怎么会错?”我马上反问:“领导怎么就不会错呢?”越是拿这样的话压我,我就越不服。
实际上,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小时候,我父母压我,我卖乖但我不服;大学里,给名教授拍马屁的学生多,但他要讲得不对,我就跟他争论,他反而喜欢你。机关要泯灭我的天性,所以我就跑了。不过,我虽然直率但我不会极端,不会让人觉得我政治上不正确,或者说伤害到领导的话。我只是就事论事,不会做让人下不来台的事。
其实,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机关毕竟还是管着很多事情的,而且通过这个工作,我明白了机关的行为模式,包括政策管理者在事情划定界限、考虑问题的思路。所以,像我们今天跟政府打交道也好,为政府服务也好,就知道这话该怎么说,事该怎么做。
机关就是小学课堂,虽然我并不喜欢背着手的感觉,但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我人生一个必经阶段。
敲敲打打的少年
口述。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
我不会忘记几十年前武汉滨江公园的那个夜晚,我和我的师兄,两个人在那里睡了一夜,那就是我木工学徒的开始。
那一年,我只有17岁。因为家境不好,只得跟随做木工的堂舅来到武汉做起了“游方木匠”。
在今天人们眼中,木匠或许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在20多年前的温州,作为当地最为盛行的两大手工业之一,当时的木匠就好比现在的博士一样吃香,一个月可以赚200块钱,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虽然我的师傅是我的堂舅,但他还是要收我的学徒费,这也是最让我伤心难过的一点。“我带一个徒弟一年要200块钱,你呢,稍微便宜一点,160块钱。”不过,这些陈年往事并没有影响如今我对舅舅的态度。
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眼中,木工活无非就是刨一刨、敲一敲,如同游戏般有趣。可才做了一个星期,看着满手磨起的水泡,我哭了。
原来当木匠是那么的辛苦,完全不是我想像的样子。半个月过去了,回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那天晚上,又被师傅骂了几句,满腹委屈的我便赌气跑到了滨江公园。陪在我身边的师兄,入门只比我早一年,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回去是不对的,你这样半个月就回去让大家多难堪,家里难堪,师傅也难堪。虽然是很苦,虽然被师傅骂了几句,但还是应该要留下。”他劝我说。
多年前滨江公园的一幕,多年后又在我身边一次次重演,只不过此后的主角变成了我和我的员工。有的员工刚开始要走,我就会想方设法弄清楚他为什么想要离开,思想工作真的很重要。
那时候城市里条件有限,很多请我们去做家具的家庭,房子都不大,住的人却不少,往往是子孙三代挤在一套两居室里。于是,我在做家具的时候,就尽可能综合多种用途,以节省空间。我们设计的桌子,既可以当饭桌,又可以当书桌,晚上将两边拉开,还可以当床用;还有电视机柜,下面有抽屉可以放杂物,中间的板子拉出来,又是一个小桌子……我们那时候的设计有些现在还设计不出来,当时做的家具有些现在依然流行。结果,我们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这家还没有做完,下一家就早早开始邀请了。
我也很快被师傅提拔为“脑力工作者——设计师”,不必再像其他的师兄弟一样每天敲敲打打做些简单的木工活,只需要找活儿,出思路、出点子。后来过了一年半左右,师傅看我特别聪明,就把原来我的几个师兄都交给我,说,你做师傅吧。于是我的几个师兄就跟着我走,变成了我的徒弟。
我始终认为,人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往往人生的某个阶段就是转折点。就在我做木匠做的非常好的时候,我有幸转移到福建某空军部队。在那里部队领导都对我特别关照。他们说你年纪轻轻又那么聪明,就不要做木匠了,去当兵吧。结果我以木匠的身份在部队里锻炼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后来我把部队的活儿交给了师兄,转而去做了比木工更省力也更能赚钱的马口铁生意,淘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待事过境迁,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我继续做木匠,相信现在会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家具公司的老板。
以前从未坐过公交车的我和师兄一起,花两块钱坐上公交车就在上海城里转,上去就不下来……之后又远赴武汉,在长江轮上度过四天三夜……其实我现在很想再去长江看一看,却苦于俗务缠身,难以成行。以前有时间但没有钱,如今有钱却没有时间,人生永远都有遗憾。
挥霍色彩的日子
口述。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当我站在这个关键的人生路口时,手里却没有任何选择权。高中毕业时正处在“文革”时期,那个年代,一切都听组织安排。
17岁,不能考大学,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锻炼一颗红心;要么进工厂,当工人。不过,这也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选择题,只能摊上哪个是哪个。
我被安排在本溪钢铁厂做煤气救护工,就是哪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就要去哪里抢修。说实话,这份工作挺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碰上煤气爆炸。不过当时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小,厂里的师傅们对我都很照顾,所以那时并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苦,反而每天都过得很高兴。
煤气工之后,我又在厂里做电工。由于有点艺术特长,我在钢铁厂时还加入了工会,办过宣传板报。我还会摄影,平时就经常被安排给大伙儿照相、放电影。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对音乐和美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小提琴、笛子、二胡、京胡、吉他……各种乐器我都能来上几下,虽然没有一个很精通的,不过我只是把它作为业余的消遣,陶冶心情就足够了。
那时候,我的房间里还常常堆满了各种颜料,喜欢自己画一些民族英雄的画像,然后把它挂起来。我还喜欢木刻,曾经自己刻过100多个毛主席头像;我能把铁板打磨成匕首,自己铸模用铁水做成铁手枪、步枪;甚至还跟一个老师傅学会了修手表、修收音机、修照相机、修摩托车……我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去做。虽然“全能选手”往往意味着泛而不精,但这些广泛的爱好培养了我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和认识。
在钢铁厂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早上很早就起床,背着相机出去拍日出。我们厂里那些习惯早起的人可能都还记得我当年高高兴兴背着相机的样子。真的,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实都挺艰苦,但当时从来没抱怨过。
事实上,从心底里就真的没觉得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人生第一份工作给我留下的是美好、愉快的记忆。直到现在,一听到那个年代的老歌,我还是立刻能记起那种每个人都充满激情的感觉。
不能自己选择工作的一个好处是,你不会存在后悔和遗憾。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想,如果当时也像现在一样可以自主择业、双向选择,我第一份工作会干什么呢?我可能会考虑去从事音乐或者绘画等艺术创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选择也不一定对我的人生发展就有好处。如果那样,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会跟计算机软件有什么关系了。
1976年,我21岁,工农兵学院来到钢铁厂选人上学,由大家推荐,谁票多谁去。可能因为我每天都开开心心,所以我当时获得的推荐票最多。于是,我就结束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光膀子的任正非面试了我
口述。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
1990年的华为不过是一家20多人规模的公司,面试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闷热,我来到深圳南油A区16栋801室。我进去后,公司老板说先冲个凉再说。一会儿功夫,老板穿着裤头,光着膀子就出来了。
他大概看了一下我的简历,因为我硕士毕业,学的是电子通讯,在兰州交通大学的时候获得过省里的科研二等奖,还在国家重点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老板很快就说,“你下午来上班吧。”
恐怕你已经猜到,这位老板就是任正非。当时工资是一个月300元钱。虽然看上去比在兰州时的一百二三十元多很多,但深圳的一碗面都要5元,可在兰州只要两毛钱。
慢慢地,我发现这个公司挺好的,任老板很能激发年轻人的激情,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未来。
开始,我做研发工作,后来又做了三年销售。做销售不容易,那时的华为不像今天市场地位这么高,我名义上是福建办事处的主任,其实从装机器到卖机器就我一个人,得陪客户吃饭、卡拉OK,因为这我学会了很多歌。
天天面对客户,天天承受失败和压力。今天失败了,明天还得微笑着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另外,销售人员要理解别人的想法和需求,要学会怎样跟别人打交道,怎样让别人认可你。对人是综合的历练。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板。任正非是一位比较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敢于投入,敢于冒险和创新。曾经有两三年时间,公司的资金跟不上,银行又提供不了贷款,任正非就以每年24%的利息向高利Dai借款,用来研发产品。当时市场上做交换机的有200多家,正是这次研发出的C004交换机为华为赢得了先机。
同时,任老板对“财”看得比较淡,他不像有些老板,公司赚钱了,先把自己兜子放满。他觉得赚钱了,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因此别人更加愿意跟他干。所以,他很早就尝试做内部期权制度。
当年老板跟我们讲故事,常常谈到他敬佩的几个人。一个是韩信,因为他能够忍受屈辱才能成就大事。这对我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人是阿庆嫂,她在商场里面八面玲珑,来的都是客,能够把关系处理好。
记得有一次,一位电信局的科员到深圳考察华为,华为当时就在居民楼,两套房子,八楼一套,九楼一套,客人来的时候没有吃饭,任老板不是请对方去饭店吃饭,而是赶紧自己亲自到厨房炒菜,客户因此非常受感动。
华为是我真正的第一份工作,让我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从20多人壮大到2万多人。
这10年,我见证了华为的变革,参与了1997年《华为基本法》的建立。有机会了解、参与整个公司管理的变革,如何面对问题,如何进行管理改进,怎么样建立系统,如何从小公司到大公司,我个人也从一名普通的研发人员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华为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真正起点。2004年我出任中华英才网总裁。
谈恋爱一样做生意
口述。红星。美凯龙总裁车建新
从前,有三个木匠,第一个木匠想,反正一辈子就同刨子、锯子打交道了,混混日子吧;第二个想,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为好木匠,多赚点钱;第三个想,我现在虽然是木工,但总有一天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于是,当他们碰上一块带结疤的木料时,第一个木匠不管好坏就凑合用上去,第二个随手扔掉换用别的木料,而第三个则把它雕刻成了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20年前,我问自己:“我是谁?”答案是:“一个好木匠。”
过了五年,我又问:“我是谁?”回答是:“一个勤劳的创业者。”
如果现在再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一个用心做事的人。”
17岁那年我离开家时,母亲把我送到门口,说了两句话:“吃西北风也要到门口去吃”,“算计不好一世穷”。
第一句话是说哪怕到了吃西北风的时候,也不能懒在家里张嘴,要站到门口去,这句话让我懂得,不吃苦,就没有好日子过;第二句话让我懂得,不巧干,就做不了大事。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还没毕业,就已经满脑子想着赚钱的事儿了。离开学校,先是到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一年后开始学做木工。
我那时特别勤快,吃饭的时候帮师傅打饭,休息的时候给他搬凳子,下班后给他洗衣服、洗鞋子,农忙的时候还到他家帮忙割稻子、麦子。这样勤快,所有的师傅、师叔们自然都很喜欢我,很愿意教我。
我很快就学会了划线、选料和配料这些基本的木工手艺,还没满师就开始带徒弟了。这样,我就把我的收入、知名度都提前抬高了。20岁时,我带的徒弟们满师了,而我自己也是这个时候才真正满师。
这时,我已经不满足于整天埋着头干木匠活了。在1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做了生平第一笔生意:打了五六个碗橱和20多个板凳,用船运到城里,再背到集市去卖。不过这笔生意失败了:我熬了几天打的碗橱和板凳只卖出了一点儿。
第一笔生意做砸了之后,我开始在路边招揽生意,在吃了许多闭门羹之后,我终于拿到了第一张家具图纸,是给一家综合市场的老板做组合家具。
但是当时我没有一点本钱,就跟姨父软磨硬泡,借来了他准备盖房的600元“巨款”,找了几个徒弟,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套搬进市场的家具,没想到很快就卖了出去,还小赚一笔。有了这个开头,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由于质量过硬,我们的家具在市场里很受欢迎,图纸越接越多,生意越来越红火。
我经常说,能谈恋爱就能做生意,为什么?先付出嘛!一个男孩在追女朋友时是最容易先付出的。做生意如果像追女朋友那样,肯定能成功。
事实上,不管做生意、做产品也好,拜师、和政界人士打交道也好,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精神,先付出,最终每个客户都会被你感动。